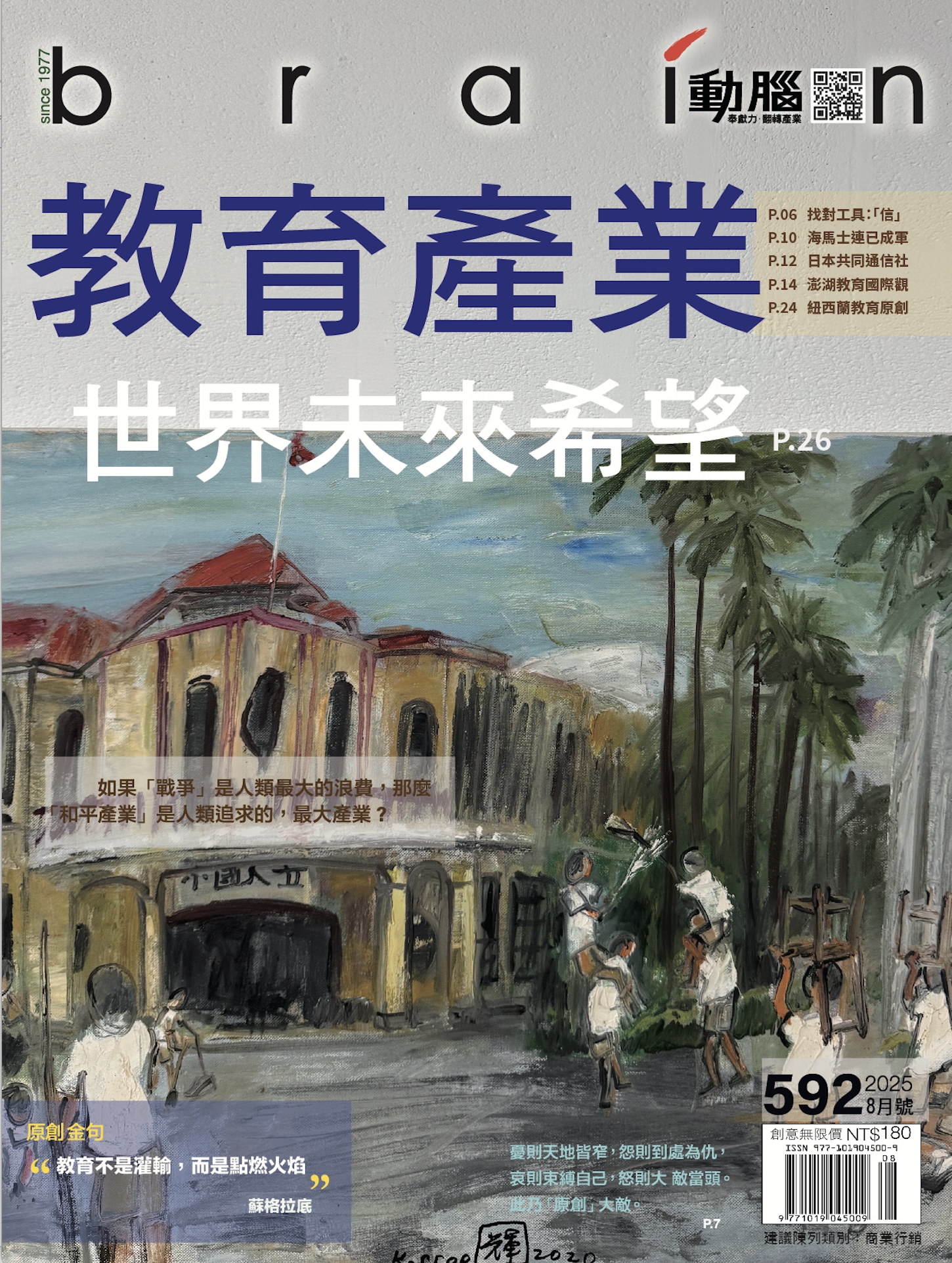台灣廣告影片製作業本來就競爭激烈﹐ 加上近年來經濟不景氣﹐使得經營難上加難。 我們不禁要問﹕製片業的春天何處尋﹖
地點﹕動腦雜誌
時間﹕2001年3月17日AM10:00~12:00
座談大綱﹕1﹑台灣製片業目前面臨的問題與對策。
2﹑廣告公司﹑製作公司和自由導演之間的互動的狀況。
3﹑對想要進入製片業的新鮮人有何建議﹖
邀談人﹕動腦雜誌社長 王彩雲
主談人﹕
光與影製作總監 王雲明
鋃頭影藝總經理 劉樹人
鋃頭影藝監製 謝國松
龔作室負責人 龔友誠(David)
聯廣公司總經理 陳薇薇
有榕乃大工作室執行創意總監 曾慧榕
環境隨時在變
王彩雲﹕經濟不景氣衝擊廣告代理業﹐也影響廣告影片製作業﹐一些廣告影片經營者甚至告訴我﹐他們的生意少了2~3成﹗今天邀請各位來﹐是希望請各位談談﹐台灣製片業現在面臨了什麼問題﹖應該要怎麼做才能開創新機會﹖
王雲明﹕我最近碰到的個案﹐大都是原本很趕﹐趕到後來又不趕﹐最後突然停掉的情形。我想是製片業間彼此連繫比較少﹐才會讓外界誤以為製片業在削價競爭。而一筆預算下來﹐剛開始在做溝通時都講得很簡單﹐但做著做著﹐要求也會愈來愈多。
劉樹人﹕其實沒有什麼預算不能執行的﹐是看你怎麼做而已。最近﹐我們發現常常會變得「瞎忙」﹐本來是20天可以交片﹐結果變成3個月才能交片﹐時間耗得很嚴重﹐這種情形對製作公司來講,是個無形的傷害。
曾慧榕﹕之前在JWT時有一次經驗是﹐客戶原來計劃某一個新產品在某個時間點上市﹐當他在做策略企劃的時候﹐這個產品還在研究的階段﹐但當時間到了﹐產品還無法上市。然而廣告公司已經和製作公司談妥﹐包括腳本﹑費用﹑甚至拍片的時間。因此大原則如果改的話﹐全部就得重新來過﹐雖有為難之處﹐可是就現實面的考量﹐卻不能不做。
陳薇薇﹕我從大陸回到台灣後發現﹐以往客戶的行銷計劃是很按部就班的﹐可是現在客戶為了反應市場變化﹐往往打亂了自己的計劃。比如說看到鑽石市場或是一些高價商品市場的商機浮現﹐就一味地投入,但投入之後,因經營模式不對,夢想很快就幻滅了。因此「做不好就收」的現象,在這一兩年特別明顯。
謝國松﹕比較在國際間和在台灣拍片的不同﹐其實我覺得製片公會很重要﹐它不只是可以排除預算的困難﹐談到費用﹐你只要指出公會的標準﹐廣告公司就比較不會跟你討價還價。如果台灣能有這個機制的話﹐製片業會比較團結。
龔友誠﹕演員的費用也是一個問題﹐兩個同樣重要的角色﹐可能會因知名度高低而有不同的價碼﹐如果演員在聊天之際知道了彼此的差異﹐那真是會天下大亂﹐根本沒有產業秩序可言。
劉樹人﹕若真要說台灣製片業出現了什麼問題﹐我想公會是個比較大的問題。我自己本身是視聽製作公會的理事﹐但廣播﹑電視﹑節目﹑廣告製作業都混在一起﹐實在是沒有辦法﹗公會可以獨立出來﹐但得有人專注去做﹐甚至犧牲工作去做。
謝國松﹕此外﹐公會也不能由某一家製片公司的老闆來負責﹐因為容易受到影響﹐可能已離開這個行業的人來做會比較中立。其實公會跟俱樂部不一樣﹐公會是一個很嚴肅的組織﹐有一個發言的權力,但也要大家認同才行﹐畢竟不是兩三個人就可以組成一個公會。美國也是有很多人不想加入公會﹐害怕受到限制﹐好像凡事都得照著標準去走。所以要成立一個公會,前提是:必須雙方你情我願。
劉樹人﹕這就是所謂的互動﹐公會與公會之間可以產生一個良性的互動﹐扮演溝通的橋樑。
曾慧榕﹕台灣製片業間橫向的連繫似乎很少﹐不像廣告公司互動較多﹐可以透過彼此的連繫﹐知道現在市場上的狀況﹐比如說這個案子有誰要去參加比稿﹑有哪些內幕......。
劉樹人﹕為什麼之前的廣告影片製作協進會一直做不起來﹐我想其中一個原因﹐是因為大家把這些當成是業務機密﹐不管在面對客戶或自身的經營上遇到了困難﹐也礙於面子不願講出來。
以一個經營者來講﹐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﹐真的有必要坐下來聊聊。例如今天是個很重要的日子﹐大家可以坐下來談談﹐但有人就寧願去參加球友會﹐因為球場上可能有生意。我想還是因為競爭的關係﹐造成這個溝通的橋樑一再斷裂。
龔友誠﹕我曾經有一陣子手上有4支片子﹐其中一支都拍好了﹐但大老闆看了之後不滿意﹐決定不收片﹐廣告公司也不付錢﹐讓底下做事的人覺得很有罪惡感﹔另外一支是因為客戶渡假去了﹐片子被拖了2個月﹐但我不過是1人公司﹐一個月就這2﹑3個客戶﹐我還是要收錢﹐但廣告公司不付﹐他們只說了一句:「我們是被客戶欺負。」所以﹐後來我離開了那個案子。
陳薇薇﹕我覺得在大陸﹐制度是比較明確的。因為那裡的環境太不確定了﹐而國際性廣告公司為了自保必須如此。我在大陸的時候﹐跟每個客戶都有簽合約﹐一回到台灣聯廣﹐卻發現很多都沒有合約﹐他們說這麼做已經20幾年了。簽約和客戶付不付錢是兩回事﹐這是對廣告代理商的尊重。
劉樹人﹕客戶不跟廣告代理商簽約﹐廣告代理商也會把他們這樣的心理轉嫁到製作公司。在台灣很奇怪﹐大家都知道這個是不對的事﹐但還是這麼做下去。
龔友誠﹕其實在每個階層裡都有不專業的人。
陳薇薇﹕如果再加上經濟環境的推波助瀾﹐原本的不專業就會整個曝露出來﹑演變成更惡質化的競爭。
我們只是路邊攤?
王彩雲﹕針對我們剛剛討論的問題﹐大家是否有什麼對策﹖
陳薇薇﹕如果我們找台灣以外的製作公司﹐所有的廣告代理商就會跟著他們的制度走﹐但只要一換成台灣的製作公司﹐就全部行不通了。
龔友誠﹕我們只是路邊攤嘛﹗便利商店標價標得清清楚楚﹐一看就知道賣多少錢﹔如果你是路邊攤﹐人家知道你是老闆就直接跟你談價錢﹐你不做就拉倒。
謝國松﹕主要心態應該是我不做﹐別人就有得做了。像我們找香港的導演﹐在電話上他們就會先問有沒有訂金﹐這是很現實的。
陳薇薇﹕這其實有專業上的勢力。
劉樹人﹕我們要先分清楚製作公司的型態有哪幾種﹖像龔作室就是導演制製作公司﹐David本身就是導演﹐經營業務可能由個人的知名度﹑魅力而來的﹔鋃頭就是製片制的﹐我們有兩個導演﹐這樣的製作公司有點像是提供服務﹐客戶會以服務好不好來決定要不要選擇跟你合作﹐而台灣有很多這樣的製作公司。
從98年開始我們就發現有同質化的現象﹐甚至有些廣告代理商會自行代替這樣的製作公司﹐決定他要的團隊﹐但他沒有注意到公司對公司比較有保障的問題﹔如果臨時組成的團隊一拍而散後﹐出了問題怎麼辦﹖但廣告公司裡的製片並不覺得很重要﹗甚至也有一些廣告公司的製片自己找國外的導演。
龔友誠﹕這也牽涉到製作公司的價值。現在的廣告公司製片﹐愈來愈多是從製片公司過去的﹐有時候他們以為自己很行﹐會有一些主觀的想法。甚至認為製片公司的一些要求是在「找麻煩」。
我曾經在合約還沒簽好之前,先被廣告公司要求做一些不花錢事情的經驗﹐但哪有事情不花錢的﹖所以我們常會跟廣告公司的製片吵架﹐因為他明明在製片公司待過﹐為什麼會不明白這些道理﹖
廣告主也應自我提升
陳薇薇﹕其實我們剛剛談到的問題﹐我覺得是廣告代理商間接造成的﹐也就是說﹐即使所有的製作公司都先向廣告代理商收取訂金﹐才去執行後續的拍攝作業﹐但沒有廣告公司和廣告主簽定合約的動力﹐廣告公司還是會想辦法去壓榨製作公司。
王彩雲﹕有沒有可能所有的製作公司沒有收到訂金﹐就集體罷工﹖
劉樹人﹕很難。在台灣開一家製作公司很簡單﹐所以對廣告公司來講﹐選擇很多。
龔友誠﹕雖然選擇很多﹐但品質好的到底有幾家﹖回過頭來說﹐問題其實在於廣告公司要求的品質也沒那麼高。只要客戶搞得懂的話﹐是不是好的導演拍其次﹐反正廣告公司又沒有堅持﹐哪個導演拍都無所謂。
陳薇薇﹕台灣本土客戶對這個行業的尊重和認同確實沒有進步;國際性客戶比較好一點。
曾慧榕﹕台灣現在的導演已經可以拍那種很精緻的廣告片了﹐創意方面或許並不很亮眼﹐但對拍片的品質有很高的要求。不過好的導演還是集中在某些人﹐即使手上有很多片子要拍﹐得排出時間﹐客戶照樣指定他拍。但這並不能普遍地提升客戶對台灣製片業的尊重。
在台灣好像大家都靠默契在做事﹐比如說在某個方面補你﹑下次補你﹐而不會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。不只是製作公司和廣告公司﹐廣告公司和廣告主也是如此﹐所有的過程都沒有制度化﹐模糊地帶太多﹐所以廣告代理商把這種會被唬弄的心理﹐也轉嫁到製作公司上。
要製作公司﹑廣告代理商一起拒絕做沒收到訂金的生意﹐我覺得太理想化。唯有廣告主和廣告公司一起去保障共同的利益﹐才有可能。
陳薇薇﹕我覺得這也是專業的問題。我們講國際性公司﹐有些品牌是國際性的﹐但執行者是當地人﹐他可能還是以當地的習慣來操作﹔而像P&G就很專業﹐不管在香港﹑大陸或是台灣﹐它都是一樣執行方式﹐可是這樣的優質廣告主畢竟還是少數。
而經濟不景氣﹐廣告代理商變成是在消化預算﹐而不是執行預算﹐「差不多」的心態比以前更嚴重。講起來台灣好像真的像是個地攤﹐只是一個區域性的市場﹐但大家應該以國際性的格局來看待﹐要求國際化的規格。
公會雖然會制定制度﹐可是還是要廣告主﹑廣告公司﹑製片公司三方面自己改進。以前我在大陸請了一位紐西蘭的導演﹐我們就得完全照他的遊戲規則去走﹐拍三天片子﹐三天天氣都不好﹐可是錢還是要付。
當然大陸本地還是會有不好的製片﹑導演﹐但也有從台灣到大陸去把規則搞亂的。以大陸網易來說﹐選哪個導演是看了全世界導演的作品來決定的﹐台灣則是一有片子就衝也似地去拍了。
以堅定原則面對客戶
王彩雲﹕我們要怎麼樣去教育台灣本土的客戶有這方面的專業呢﹖
謝國松﹕我覺得製片公司比較難。其實問題還是卡在廣告公司﹐因為做生意嘛﹐他不可能因為收不到客戶的訂金就不接這個案子﹐還是要承受這些風險。而我們製片業不可能直接跟廣告主說:「你不給錢就不拍。」所以變成一種惡性循環。
我覺得廣告代理商自己應該要勇於承擔風險﹐而不能自己收不到錢﹐就不付給製作公司訂金。
劉樹人﹕不過有些廣告公司實在是很棒﹐即使廣告客戶不付訂金﹐仍會付訂金給製片公司。
陳薇薇﹕以奧美來說﹐在大陸﹐奧美有付給製作公司訂金﹐但回來台灣﹐我才發現聯廣給製作公司的訂金都是代墊的。不過我們已在改善這個現象。
曾慧榕﹕我以前在大陸遇過一種狀況﹐明天要拍片了﹐今天還沒拿到錢﹐那時的製片就給廣告公司兩個選擇﹐不給錢就取消。他們在大陸是有這個勇氣跟客戶說這種話的。可能是因為他們在大陸觀摩了很多﹐知道原則是什麼。所以我認為台灣的製片公司可以到香港去看看﹐香港製片公司強悍多了。
龔友誠﹕不過這樣的導演就會被人家說成「很難搞」。像我就常常被廣告公司找去想idea﹐因為我想得快﹔這兩三年來﹐當他們來找我﹐我接到電話第一句說的就是:「先來個20萬我才做。」漸漸地﹐就沒有人來找我了。
王彩雲﹕以紐西蘭來說﹐雖只是個擁有300多萬人口的市場﹐但不論是廣告主﹑廣告公司或製片業﹐都很有制度﹐為什麼有2,300萬人口的台灣不行﹖
龔友誠﹕這從騎機車就可以看出來了﹐爸爸帶著小孩紅燈右轉﹐警察看到也不管﹐習慣養成之後就很難改。我覺得要改變就得從最基本的教育﹑文化改起﹐不過要看到成果也是20年之後了。
陳薇薇﹕還有,真正的專業是不分國籍的。
建立夥伴關係
王彩雲﹕廣告公司和製片公司和自由導演之間的互動有沒有問題﹖
王雲明﹕有些導演拍片拍一拍﹐因為覺得把製片公司的製作費都花掉了﹐覺得不好意思﹐乾脆自己開公司。
劉樹人﹕就鋃頭來講﹐我們有自己的導演﹐我們配合的導演不是自由導演就是簽約的導演﹐分別來自台灣﹑香港﹑馬來西亞﹑泰國﹑印度﹐就屬台灣的導演最奇怪﹐他希望自己每一種商品都可以拍﹐不願意被定型﹐既可以幫這家拍﹐也可以幫那家﹐價值觀不一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﹐說什麼製片公司有多專業﹑製片團隊能力有多強﹐都是空談。
所以基本上﹐廣告公司在選擇製作公司時要考慮﹐製片和導演的默契是有關係的﹐但大多數人都只想到導演。
曾慧榕﹕像龔作室的導演自己就是老闆﹐大概沒什麼問題﹐但當我們在選導演時﹐也會去徵詢他所屬意的製片公司﹐即使他是自由導演還是會有偏好﹐這樣的案子就可找到導演喜歡的那家製片公司來合作。不過來者不拒的自由導演是不是也會體認到合作的不愉快﹐還是只要有案子就接﹑有生意就做呢﹖
劉樹人﹕我也在思考為什麼台灣的導演什麼領域都想拍。主要原因是可以賺更多錢﹑也有更多的腳本可以選擇。腳本的量可以滿足成就﹐拍大量的片子就可以以量制價。而像龔作室就會控制它拍的片量。
龔友誠﹕這又回到最初的問題﹐因為預算只有那麼多﹐如果一位導演你估價是50萬台幣﹐那這筆預算一定會被刪。說實在的﹐台灣好的導演實在不多﹑創意也不多。
陳薇薇﹕也就是沒有足夠的經濟去養成一個好導演﹐為了求生存﹐只好不斷接案子。我這次回來台灣﹐發現有幾個導演一直在退步﹐不像以前那麼銳利。
龔友誠﹕因為體制不健康啊﹗我曾經遇過一種情況是﹐廣告公司給我一筆預算﹐我後來才知道那是拍兩部片子﹐而不是一部片子的經費。
陳薇薇﹕廣告代理商跟製片公司的關係首先一定要平等﹐而且一定要尊重專業。聯廣可能因為有些客戶比較惡質﹐形成聯廣過去在作業上的惡質化。以我在大陸的經驗﹐我也曾經遇到客戶不付錢的例子﹐當時片子在我手上﹐我就是堅持不交片﹐致使雙方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。
解決問題其實有很多方法﹐比如說要求客戶背書﹐載明何時會付清費用﹔一定要有個原則﹑立場。但讓人難過的是﹐這明明是個對的事情﹐為什麼不能這樣做﹖在台灣﹐所有的聲音都會告訴我﹕「我們這樣做已經做很久了。」這絕對不只是聯廣﹐而是台灣整體環境出了問題。有人還告訴我﹕「妳不要這麼硬﹑不要這麼有原則﹐事情就是這樣﹐這個客戶這麼好﹐不要簽約沒有關係......。」這是一種專業態度。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﹐為什麼我們還是用18﹑19世紀的態度在作業﹖
劉樹人﹕其實類似這樣的座談會我們也談了很多次﹐但還是沒辦法立即解決這個問題。
陳薇薇﹕但我覺得跟台灣的導演或製片合作﹐優於香港。就導演而言﹐香港的導演是不會全程參與的﹐他只負責把你的腳本很準確地拍出來﹐剪接後他也只看個大概﹔可是台灣的導演會全程參與﹐把他的想法注入整支廣告片中﹐個人也會去詮釋創意﹔所以創意人員應該把導演看做是「工作夥伴」﹐共同去呈現影片最好的一面﹐而不單單只是去執行某一個腳本。這就是我們在大陸找導演時會考慮的﹐他對創意的完成性很高﹐但在詮釋上我就得想得更完整。
劉樹人﹕其實台灣的導演是很好的﹐但環境的影響﹐逼得他們必須把價錢開得很低。以前我們也和陳薇薇合作過﹐真是夥伴的關係﹐我們現在也一直在尋找那樣的快感﹐並不是我們懷念過去﹑不求進步﹐而是這個工作本身就是要有熱情﹐才能激盪出一些火花。
我想建構「夥伴」關係最重要的關鍵在於﹐創意人員是不是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。創意人員常常會說得很好聽﹐要導演來加分﹐而加分的結果是創意人員往往忘了自己的初衷﹔但創意的背後其實是要有策略的。
龔友誠﹕以我在英國拍片的經驗﹐發揮的空間真的較大﹐雖然預算有時候比較緊﹐但基本上都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去做﹐甚至導演可以參與選角﹔但在台灣﹐導演沒有辦法學到很多﹐廣告公司的創意人員也沒時間去跟片﹐看導演是怎麼樣選角的﹔香港的創意人員則會全場從頭跟到尾﹐同樣的﹐創意人員也可以學到很多。而以我導演的角色﹐我會很希望我能真正了解﹐究竟創意人員要賦予這個廣告什麼樣的情感。台灣這樣環境對導演來說是好的﹐但對廣告主來講﹐未必是好的。
劉樹人﹕其實導演的工作並不是要涉入到創意裡。像香港或其他國家的拍片環境是健康的﹐但台灣還沒做到健康就把空間開放得那麼大﹔就像台灣社會的自由﹐其實是已經過度的自由了。
陳薇薇﹕一個夠資深的創意人員和一個好的導演互動時﹐創意人員的腳本和最後製作出來的片子﹐其實是不會差異太大的﹐因為資深的創意人員會很清楚地知道他要表現的是什麼﹐他會堅持。
龔友誠﹕的確﹐在其他國家拍片我只照腳本拍﹐但在台灣我發現照著腳本拍沒用﹐因為你要求的東西到了現場不一定都有﹐以前借得到的場地現在也不一定借得到......。因為預算不夠﹐你在巴黎﹑在書上找得到的道具﹐在台灣不一定找得到﹐還要花錢去做﹑並趕出來。所以我在台灣拍片都是在「趕」﹐如果照著腳本拍就都完了。我在台灣是被逼得得這樣做﹐我也覺得這樣才有創意空間﹐但是導演或是創意人員其中一個一定要很清楚﹑夠強勢。
充實對人文的感受度
王彩雲﹕這樣看來台灣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地方﹗接下來請大家給想進入這個行業的新鮮人一些建議。
龔友誠﹕我之前在面試一些新人﹐結果有幾個我都奉勸他不要來做。一般外界在看這個行業﹐不管是拍電影或廣告影片﹐某些程度上是有些浪漫﹐但實際上做起來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人做的﹗除非是他們真的想清楚﹐所以會有個試用期。但我也發現學校的教育可能出了一些問題﹐沒有告訴學生這個行業很苦的地方。
曾慧榕﹕我剛好在南部學校裡有兼課﹐學生們會擔心將來畢業後可能不好找工作﹐想去大陸。但我覺得﹐一個剛畢業﹑還不成熟的學生去大陸﹐同樣和一群人在競爭﹐條件也不比別人強﹐人家要不要用你﹖所以還是先從台灣起步比較好。
而不管是專業技術﹐可以透過在學校或日後在工作上的經驗增強﹐但最後的關鍵仍在於「對人文的感受度﹑掌握度與表達」。當初我離開大陸回來台灣前﹐當地的人問我可以提供他們什麼建議﹐我說創意或執行上的技巧很容易就可以達到﹐以機器設備來說﹐他們可以獲得最新的﹐但決勝點還是在於他們對人文的觀察與體會﹔在學校的學生也是如此。而這種更高一層的培養可以很多元﹔不過﹐懶人是絕對不會有創意的﹐至於關注什麼課題﹐則來自個人的個性和興趣。
劉樹人﹕我覺得真的是要弄清楚﹐如果你有理想﹑有目標可以去做電影﹐如果你想賺錢就去做廣告﹐什麼都沒有的話你就去做電視。現在在台灣做這個行業已經是很危險的了﹐可是沈浸在執行過程中你會特別感動﹐就像做廣告創意和電影一樣﹐從發想到執行可能要花好幾個月以後﹐到真正上片了又是好幾個月﹐但當你看到成果後會真的很感動。
我每年都會接觸到一些新鮮人要投入這個行業﹐但就我們早先談的違規和違法的情形﹐他們會覺得奇怪﹐為什麼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還能做這麼久﹖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由師範大學舉行的座談會﹐在會中﹐我發覺學校的教授灌輸給學生的觀念﹐和實際的職場差異很大﹔所以我建議學校要常常更新教科書﹑跟上業界的腳步。否則有些人的素質很好﹐卻不了解現況;也就是這個環境雖然不至於違法﹐但他們正在做違規的事﹗
龔友誠﹕從得獎作品的這件事來說﹐其實我們知道有些作品得獎是政治因素﹐但學生會把那些作品奉為圭臬。我建議新鮮人第一要確認自己是不是很用功﹐再來要找到一個學習的對象﹐要很用心地去體認工作﹐不要設立那種要去哪家廣告公司的目標﹐或者是把履歷表隨便撒﹐有回音的你就去了﹐那可能會浪費個半年。確認目標﹑找到學習的對象很重要﹐另外就是要加強語言能力。
陳薇薇﹕我看到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是向「錢」看﹐而不是向「前」看﹐其實他們的素質比我們當年好﹐能夠分享到很多資源﹐但他們很急﹐不是急著學習﹐而是急著要成名﹑賺很多錢﹐或許是環境讓人變得沒有耐性﹐但不要讓它變成缺點﹐是轉換成更積極地去學習﹐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很多閱歷。
將來10年內英文還是主流語言﹐對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是基本配備﹐不是競爭優勢。而製片業的環境還不像廣告公司已經有很明確的機制﹐所以跟對一個好的團隊﹐比較容易了解作業面。
謝國松﹕現在的世界已經是不分國界了﹐尤其透過網路﹐更可以拓展視野﹐新鮮人應該用比較大的格局來思考﹐而不只是侷限在台灣或一個國家。
龔友誠﹕還要學會「思考」﹐現在人很會抄﹐但是愈到後來﹐條件會愈不一樣﹐你是沒有辦法再複製的﹐如果你不會想﹐那會有很多問題是很難克服的﹐因為製作過程本身就是要解決很多問題。
陳薇薇﹕這也是他們都急著要成名的關係﹐用抄的最快﹗
龔友誠﹕甚至我們也會發現﹐很多得獎作品也是用抄的﹐以一個創意人員來講﹐你多抄幾個作品就可以當創意總監了﹗
陳薇薇﹕在台灣的創意總監可以這樣混﹐但到大陸去﹐客戶會用創意總監的標準去要求你﹐所以你沒辦法用混的﹑會立刻掛掉的。
王彩雲﹕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﹐將來如果有任何意見﹐或在工作上有不平之鳴﹐歡迎隨時與動腦連絡。(動腦張文娟錄音整理)
《資料來源:動腦雜誌301期2001年5月》